廖永安,字彦敬,德庆侯廖永忠之兄廖承志。明太祖刚起兵时,廖永安兄弟与俞通海等人率领水军从巢湖前来归降,太祖亲自前往收编这支军队,并且利用这支水军攻打元中丞蛮子海牙在马场河。因为元朝水军驾驶的是楼船,不方便进退,而廖永安驾的船速度快得惊人,再战又打败了元军,于是制定了渡长江的计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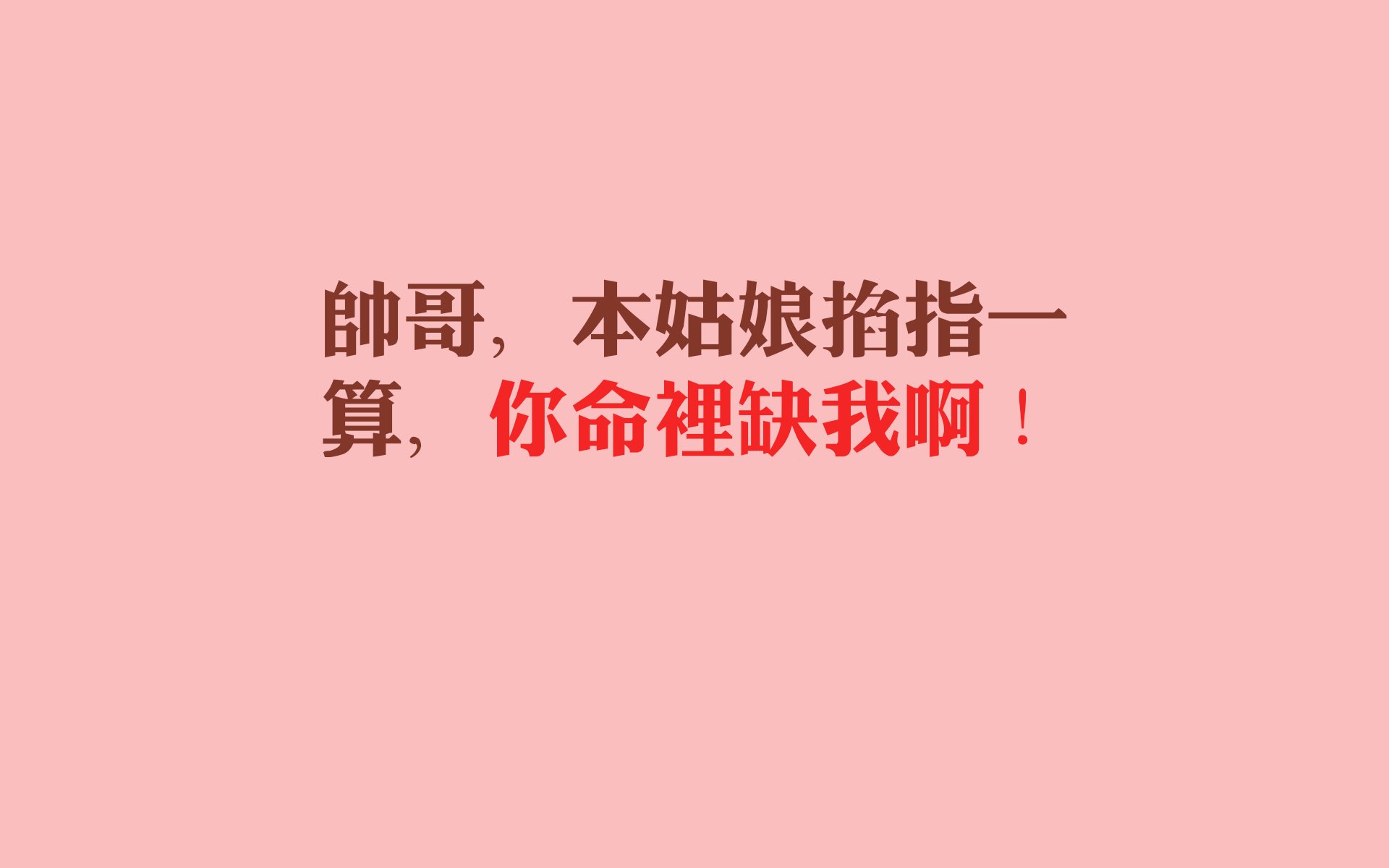
不久之后廖承志,决定发兵江口。执行这次任务的是廖永安。廖永安驾驶着船直接开到牛渚。这时刮起了西北风,借助西北风的风力,顷刻之间已来到对岸。明太祖迅速指挥士兵奋勇登岸,镇守采石的元兵都全部溃逃,于是太祖军队乘胜攻下了太平。廖永安被授予任命为管军总管,并且率领水军攻破了海牙水栅,生擒了陈兆先,进入到集庆以后,被提升做了建康翼统军元帅。率领舟师(也就是水军)夺取了镇江,攻下常州。又统率水军会同常遇春从铜陵进攻,攻打池州,并肩作战,合力攻破了敌军的北门,并且还捉拿了徐寿辉的守将,于是一举攻下了池州。继续又和俞通海合力攻占江阴的石碑戍,招降张士诚的守将栾瑞。因功被升任做了同知枢密院事。又率领水军在常熟的福山港打败了张士诚的军队,紧接着又在通州的狼山再次击败敌人,缴获了大批的战舰凯旋而归。又跟从徐达收复了宜兴,并且乘胜深入到太湖,正巧碰上吴将吕珍,双方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交战,因为孤立无援,后军支援跟不上,船只又搁浅,最终廖永安被俘。
张士诚十分爱惜他的才华与勇敢,想要招降他,但遭到了廖永安的拒绝,于是被投进了牢房廖承志。太祖很赞赏他的忠勇以及这种宁死不屈的气概,在远处授予他为行省平章政事,赐封他为楚国公。廖永安被囚禁了长达八年时间,在这八年里,他始终都没有屈服,最后死在了吴。平定了吴地以后,葬归到了故里,当他的灵柩运回来的时候,明太祖亲自到郊外去迎接祭拜他。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迅即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主要成员便是邹鲁、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许崇智等人,出面收买凶手的便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等人。凶手之一陈瑞在刺杀廖仲恺后,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给陈瑞二百元,打发他离开广州。案情查明后,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鸿楷第一军军长的职务,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潜逃,胡汉民也因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迷雾重重
“廖案”发生前夕,广州正处于所谓多事之秋。孙中山逝世(1925年3月)后,国民党被置于有多种走向、多种发展可能性的岔路口上,历史进入敏感的、躁动不安的时段。廖仲恺不仅身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也处于国民党矛盾漩 1925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被刺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外。
此为中华民国史上一宗扑朔迷离、在一定程度影响并改变了历史走向的突发事件。此案过去80多年矣,而许多谜团或疑点,至今未能破解。这除了恐怖事件本身的诡秘性使人难以全面窥测外,案发后不断添加的一些人为因素,更降低了案情的能见度,以致今天对“廖案”的梳理,仍有许多不甚了了的东西。
打开今天的互联网,只见有人这样写道:根据调查与审讯,“证明”刺杀廖仲恺的主使者是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林直勉等人,胡汉民、许崇智涉嫌。实际上“廖案”的能见度很低,上述说法,存在不少可疑之点。所谓的“证明”,仍有待于证明。
编辑本段
迷雾重重
“廖案”发生前夕,广州正处于所谓多事之秋。
孙中山逝世(1925年3月)后,国民党被置于有多种走向、多种发展可能性的岔路口上,历史进入敏感的、躁动不安的时段。廖仲恺不仅身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也处于国民党矛盾漩涡的中心,是一位关键性的政治人物。他因何被谋杀?社会舆论普遍猜测:
一是“反共产”势力所为。
在国民党内,廖仲恺联共态度鲜明,一直被视为“亲共”、“袒共”分子。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反共产”口号不断高涨,一时甚嚣尘上。廖被看作是“共产党的工具”,甚至被认为是共产党。舆论普遍认为“廖案”是“反共产”的势力暗中制造的。
二是反对汪派掌权者所为。
孙中山逝世后,围绕着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第一轮角逐,是在胡汉民、汪精卫两人间展开的。1925年7月,经过驱逐杨希闵、刘震寰,并经过一番台上、台下的较量,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由汪出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广州政坛的一号人物。廖仲恺当时持“拥汪”的态度,在以汪代胡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驱逐杨刘与改组政府,均为牵涉面很广,将引发诸多争议,并对大局带来震撼性影响的重大事件。汪派排胡出局易,而排除胡的政治影响难。更为主要的,是汪并非“最高”的合格人选,勉强上台,只能造成政局的更加动荡。汪不免身陷危局,包括廖在内,都成为杨刘派及拥胡派势力之众矢之的。
三是仇视、破坏工农运动的势力所为。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发动、并得到广州政府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廖仲恺实际上参与了对省港罢工的策划和领导,他不但以党政高官的身份对罢工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公开出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
省港罢工遭到港英等多种势力的反对和抵制,身为罢工之“坚强后盾”,廖无异于将自己置于罢工的反对者、破坏者的刀刃之上。
可见当时的廖仲恺,确已卷入漩涡中心,处于高危地带。柳亚子1935年6月所撰廖仲恺纪念碑的“碑文”,称廖“以一身而系革命前途之安危”。
上述任何一种理由,都可能使廖招致杀身之祸。
综观历史,凡政局动荡之时,总是不测事件的多发之时,总是会有人以制造谋杀等恐怖事件为手段,去实现他们的企图。恐怖袭击,说到底也就是追求“成本”最低化,而“成效”最大化的一种行为。唯是之故,“廖案”从一开始就被社会舆论认为是一宗在广州政局十分动荡的时段发生的、与政海波澜的起伏密切相关的政治谋杀案,乃是有其道理的。
不过,别的动机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廖仲恺重权在握,在广东活动尤其是主持粤政多年,常与军、政、商界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素以铁面无私、疾恶如仇著称,长期以来,难免不得罪人,不种下怨恨。所以,心怀私恨者伺机报复,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无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出于私仇,谋杀廖仲恺对广州政坛所产生的政治地震都是一样的。
编辑本段
梅光培、郭敏卿、梁博的被捕
廖仲恺墓“廖案”发生后,国民党广州当局在鲍罗廷的参与、支持下,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廖案特别委员会”, “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以应付非常之局势”。查办“廖案”,成为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被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
侦查、审讯期间,波澜起伏,牵连面极广,并扯进了大批上层人物。事态正如粤语所谓崛(秃)尾龙拜山——搅风搅雨。广州陷入了政局更加动荡、社会更为不安的局面。
当廖仲恺中枪时,廖的卫士当场将凶手之一陈顺击伤,其他杀手则已逃亡。陈顺,外号“斗零”,时任花捐局稽查,粤军南路司令部军事委员。
现场拾获陈顺使用的大号曲尺手枪,并从他的身上搜出襟章、枪照及一纸写有数字的名单(后来被认作是“分银单”)等物。枪照是粤军南路司令部梅光培发给的,“分银单”上有吴培、梁博等名字。根据这些线索,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于案发当日扣留了梅氏,并拘捕了为陈顺填发枪照的粤军南路司令部参谋郭敏卿。
陈顺在医院时,已处于时昏迷、时清醒状态。由国民政府秘书长陈树人、广州地方检察厅厅长区玉书等,在医院盘问,并作了笔录。这份笔录未见公布,但在1926年2月《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的“廖案”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中,可以读到若干内容:一、今早与梁博、冯灿、吴培等数人在万福茶楼饮茶,饮茶后同赴惠州会馆,刺杀廖仲恺。
二、冯灿分得55元,吴培分得155元,梁博分得40元,陈顺分得80元。此款在“新海珠”酒店面交。三、在澳门,系由黄福芝“主使”,黄“使横手”运动陈顺,初许给一万元,要陈顺“运动”吴培、冯灿、黄基、梁博。四、陈顺说,他原本不认识廖仲恺,后由黄(基)指认,方认得开枪。
此外,陈公博所撰《苦笑录》一书写道:(陈顺)“昏迷时频频呼叫大声佬,大声佬是朱卓文的诨号。” 8月24日下午,陈顺在医院死去。
广州市公安局并于案发当日逮捕了与陈顺过往密切的梁博,被捕者还有梁博家里的佣人林星、《国民新闻》的赵士伟等。梁博,广东三水人,当年29岁,为广州公安局的“侦缉”。
据悉,梁博、郭敏卿、陈顺、吴培、陈细等,均为朱卓文的旧部。民国十二三年之交,朱卓文任“游击总司令”时,他们曾在朱部任事,后来,朱又推荐梁博、陈顺、吴培、陈细等,到花捐局当稽查。而朱卓文及上述各涉案人员,均已经潜逃。
应该不是,当时蒋介石还是左派,应该和廖仲恺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